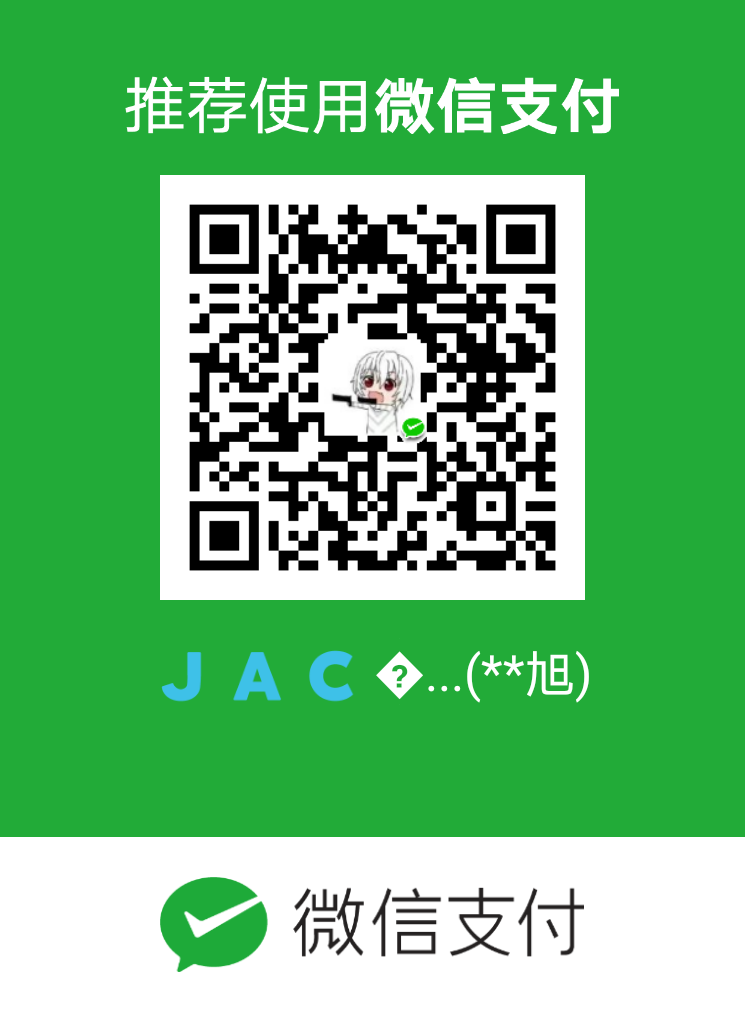我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什么了。
其实很奇怪,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不怎么爱动脑,不怎么爱思考的人,或者说,这是从小被别人打上的思想钢印。
上了大学,偶然间跟一个“新”朋友分享了些看起来很显而易见的想法,她居然很认真的称赞说我想的很深刻。
希望她是认真的吧,至少我很受用。
正如在日神精神一篇里提到的,从现在来看,我小时候的环境让我养成了胡思乱想的习惯,这种胡思乱想在中二病的浪潮退去后,进一步深入与发散,让我开始想些更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习惯究竟是对我的馈赠还是毒害,因为它从来对我的外在性格表现没有影响——不希望别人认为我是一个无病呻吟的网抑云青年,于是它只是和无数其他因素一起塑造着我的潜意识,而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今年暑假,从遵义飞北京,空中遭遇气流颠簸,这对于一架737窄体机当然很常见,也不是很剧烈,但我却——几乎是平生第一次 感受到了对死亡的恐惧,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贯穿全身的恐惧感。而你却还要强装镇定——你不希望表现得比旁边跟你搭话说自己儿子考400分这是自己平生第一次坐飞机的胖子更惊恐。而这种恐惧,之前只有过一次——高三的一个晚上,梦到一把刀子扎穿自己心脏,鲜血如注,及时赶到医生说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看着我死去。飞机上,我不止一次的点开手机备忘录,想要写些什么,但大脑却一片空白——当你就要死了,你会给世界留下什么?之前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回到北京后,我一次次的询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如此害怕?即使是一年前的西安之旅,我也没有如此担忧。更往前,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暴风雨夜,遵义新舟机场,进近,降落,复飞,进近,降落,复飞,反方向进近,降落,成功。无尽的盘旋和复飞中,我却只觉得有意思,以至于后面每次飞行都期待着发生突发情况,飞机紧急迫降,想想就感觉很刺激。
但这次,却截然相反了。也许是某种管理恐惧的激素的褪去——他们管这叫成长;也许是对于我的18岁,我的大学生活,我的大好人生还未开始就要结束了的遗憾;也许是对死亡…不,没有也许,我没有对死亡之后未知的恐惧——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知识和理智告诉我死亡之后什么也没有。但是,在飞机上,我的确理解了,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拥有宗教信仰——这是一个我之前没有细想过的问题。在那觉得自己随时会死的2个小时里,我不止一次的在胸前画十字架,不止一次的想,我要是能虔诚地信一个宗教该多好啊,譬如基督教,我知道我肯定会去天堂或地狱,无论哪里,至少我还能够“我思故我在”,从这个角度想,我还是存在的,甚至都不能定义我是否真的算“死了”,而不是由冷酷无情的的自然法则决定的,人作为一个低熵的有机物,和周遭物质从根本上没有区别,人甚至无法知道自己死了!恐怕这才是最绝望的吧,人的肉体和意识同步存在与湮灭,飞机坠毁的一瞬间,肉体毁灭,我的意识还不知道我已死就消失了,难道不是很可怕吗?机上的两个小时里,我试图去如同租借女友一般租借一个宗教,让他占据我的心,但我的理智却始终存在,顽固不化的告诉我宗教的一切不过是禁不起推敲的泡沫罢了,可惜我对基督教教义不了解,完全无法反驳我的理智给出的质问(所以后来我在去美国的时候买了本圣经),于是一切只便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了。
我只是经历了2个小时的折磨,而古人们许多每天都游走在生死的边界,那么压制自己的理智,将宗教作为唯一的寄托,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甚至赞成的了。
再往前一点,且不提儿时不堪的回忆,我却也有过想死的经历。今年三月一晚,刚刚变成过敏性体质的我吃下了一盒此前从未尝过的神秘水果。老实说,还未咽下我就知道不对——因为我根本咽不下去。果子卡在了喉咙里,为何?过敏引起的喉头水肿。随后浑身的瘙痒让我确认我大约的确是过敏了。不幸的是,家里人会开车的又都喝酒了——“出租车,北医三院”。路上,我经历了迄今为止最难熬的十几分钟,瘙痒,晕眩,恶心,呕吐;还没到地方,我的胃就已经清空了,但这种生理性、刻在人类进化基因里的、面对可能毒物的反胃恶心却从未离开,我必须说这种功能在现代人类社会是非常无用以至于有害的——至少它让我想死。到医院,下车,我已经几乎看不见了,面前的一切像是我的action5p一样充满了噪点,所有声音好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肌肉也已几乎不能控制。我倒在抢救室门口,被担架抬了进去。
但我仅存的内心是庆幸的,至少我不会真的死了。血检——血压太低,血液甚至无法被正常抽出。肾上腺素,地塞米松,葡萄糖,氯化钾…晕眩和反胃逐渐消失,我好像重获新生。一个半小时后,我血压已恢复正常,但医生却让我明早检查后再离开。好消息是明天周日不用上学,坏消息是我将被迫在这个灯火通明的抢救室中度过这注定难熬的一晚。抢救室里大部分都是老人,他们此起彼伏的叫嚷着,像是在进行某种古老而虔诚的仪式。一个老人恳求着值班护士再给他一片止痛药,但他半小时前刚服用完,疼痛不能通过药片抑制,就只能用嘴巴来缓解了;一个老人向他的儿子哭诉自己腿部的疼痛,儿子无奈地说着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话——跑了三家医院都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于是疼痛无法找到源头,只能通过嘴巴来表明自己的存在了。那一晚,我只睡了一个小时。不知是抢救室的灯光太耀眼,还是老人们的叫嚷太吵闹,又或者是我胡思乱想了太多——在这里,对生和死的追求标准变得模糊。从小学到高中,接触的更多,看到的苦难也更多,绝对理性的角度看,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苦难不是平均的,有些人注定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痛苦,甚至于犹如霍金之类,几近完全丧失与外界交互能力,又或是空鼻症等无时无刻不被无法忍受之痛所折磨,那么对于他们死>生的价值判断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他们却有人依然选择活下来,将生置于死之前,造成差异的核心我认为在于对于人生意义的探寻,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和设立。当然,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但是我想说,人生之意义是A还是B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而非先验的标准;因而没有一个绝对的对与错,每一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是有意义的,每个人都走着他们自己选择的路。
以上,只是我在一个下雨的夜晚,花几个小时给自己写了些故作深沉,我也搞不太懂的话罢了,越写越觉后悔为何不早些动笔。彼时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但却也给我想到哪写到哪的机会,这叫意识流吗?也许我应该去看看高中同学推荐的《到灯塔去》了。